普利兹克建筑奖(以下简称普奖)是世界范围内最具权威的国际性奖项,被誉为建筑界最高荣誉,以授予一位或多位建筑师,表彰他们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才智、想象力和责任感等优秀品质,以及通过建筑艺术对人文科学和建筑环境所做出的持久而杰出的贡献。
2020年,伊冯·法雷尔和谢莉·麦克纳马拉成为了普奖新晋得主,她们是爱尔兰的女性建筑师,发轫于都柏林(爱尔兰首都),共营着格拉夫顿建筑师事务所,实践横跨爱尔兰国内与国际,除了作品的优秀,她们亦以建筑学核心的思辨为始,提升至价值观与思想的构建,阐述着社区与公民意识、文化的连接、道德的锚固、慷慨与回馈的赠予等人文词语之于建筑的思考与生成,并以结构先行对建筑一切的赋予,创造出空间的开放与自由,光影的灵动与迷离,也以对地球负责为已任,关注着气候变化、自然资源、对环境敬畏、城市复兴与贡献等议题,最终展现建筑的真诚、平凡与谦逊,以及富有人文意识。
而普奖从创立至今已举办了四十四年(1979年-2022年),历届获奖建筑师皆是一时之选,更是建筑之于时代的引领,其高度不言自明、无庸赘述,获得普奖成为了众多建筑师的追求,在攀上高峰之前予以自我的鞭策,而普奖也借此激发建筑界更多的关注与讨论,以及更大的创造;而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身处众多获奖者之中,代表着某一部份的话语,而历届普奖的授予也说明着普奖评判想要传递给外界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是关于时代、潮流、参照、维度、范式或是议题,还是关于文化?以及建筑在未来的角色。
那么,为了对普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回顾和审视普奖是为必须,以洞察其演进与评判轨迹,以及信息的传递,若以10年为一个阶段的观察期,将会发现其中蜕变的回应以及价值取向与意义的内容凝聚。
一 以美国居多、欧洲其次、再来亚洲
(1979年-1989年)
首先,在1979创立那年与20世纪80年代(1980年-1989年)里,普奖得主来自世界各大洲,分别是北美洲的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1979年获奖,美国)、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raging,1980年获奖,墨西哥)、贝聿铭(Ieoh Ming Pei,1983年获奖,美国,华人)、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1984年获奖,美国)、戈登·邦夏(Gordon Bunshaft,1988年获奖,美国)和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1989年获奖,生于加拿大,美国),南美洲的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1988年获奖,巴西),西欧的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1981年获奖,英国)和凯文·洛奇(Kevin Roche,1982年获奖,生于爱尔兰,美国),中欧的汉斯·霍莱因(Hans Hollein,1985年获奖,奥地利)和戈特弗里德·玻姆(Gottfried Böhm,1986年获奖,德国),东亚的丹下健三(Kenzo Tange,1987年获奖,日本)。
由上可知,普奖在这个阶段(1979年-1989年)的得主以美洲居多,7位,欧洲其次,4位,再来亚洲,1位,而就国家区分,美国有6位,墨西哥、英国、奥地利、德国、日本、巴西则各1位,所以普奖在这个阶段(1979年-1989年)的授予以美国建筑师居多,其中约翰逊是普奖首位获得者,隔年就担任评委,而首届任普奖评委的矶崎新在2019年获奖,1983年的贝聿铭则是美籍华人首次获奖,普奖也在1988年首次授予给两位,尼迈耶和邦夏,而1982年获奖的洛奇在1983年加入评委阵容,1984年加入评委阵容的槙文彦在1993年获奖,而普奖也自1987年起增颁铜质奖章一枚。
二 创立于多元,择以精英,旋涡中的差异
若更清楚的界定,普奖表彰的是建筑师(在世)获奖的当年及其过往的实践,并在无关国籍、种族、宗教或思想的前提之下进行的;而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的普奖在其创立那年(1979年),正处于20世纪70年代末,也正是现代主义式微,晚期现代主义、高技和新理性主义的延续,与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以及解构主义初探的多元时期,此多元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处于后现代的兼容并蓄与多样之中,在欧美资本的文化体制(不包括苏联与东欧的社会)里,美国也就成了建筑潮流的中心,众多建筑师追逐其中,喧哗众声,百花齐放,而普奖则以符合专业、潮流与价值的从优选出具代表性,择以精英式的公布,而其烘托的成果也绝非以上思潮的一尘,而是体现拔萃后的差异,反映在普奖得主的实践上。首先,在晚期现代主义旋涡中前进的是约翰逊、迈耶、贝聿铭和邦夏。约翰逊以材料的精确、精简的结构、严谨的比例与优雅的匠艺来完成在现代(形式与空间)的多面向探索,在获奖的同时,对思潮演变敏感的他正向后现代呼喊着,并大胆地从过往突围,以取得自由来对经典传统有所隐喻(图1)。而坚守现代的迈耶,其实践潜心于白色寓意的阐明,关注动静演化的空间结构(尺度、等级、景物与光影),及其与体量、与光组合所呈现的纯净、脱俗与和谐,形式是富有鉴赏的(图2)。而贝聿铭也以现代形式做为对外的表述,有分寸地留意丰富、重复与带有某种意象的几何关系,运用了光与空间的相生、材料的研究、结构与装饰的融合以及人的活动与仰望来为其建筑增添艺术的尊贵(图3)。而从不避讳其商业出身的邦夏,其实践也在现代形式的基础上对技术与工程有所贡献,创造性地提出预制装配以及新材料与空调等技术赋予高层的创新,让建筑提升了质量,也兼具美学与功能的标准示范(图4)。
图1:美国加登格罗夫水晶大教堂,菲利普·约翰逊
图2:美国亚特兰大崇高艺术博物馆,理查德·迈耶
图3: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贝聿铭
图4:美国耶鲁大学珍品图书馆,戈登·邦夏
而丹下健三同以上几位也是崇尚现代,亦是新陈代谢运动的强力支持者,其实践以探求传统的观点对现代的城市、环境与纪念性有所回应,提出功能理性之于象征原型的运用,以及把材料、结构与形式予以融合的焕发出带有传统余韵的现代,而之后探究着空间与社会结构关系以及智能技术的获取(图5)。
接着,斯特林和霍莱因用倾向于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站稳了与现代主义的博弈。斯特林以抓住历史、地域风情与符号并存的人文信息为其实践的重点,以追随高技的特征把建筑创造出灵活而有机,进行平面与空间的复杂对话,让建筑成为集合体,揉合了功能、尺度与情感,赋予其艺术性(图6)。而霍莱因则以建筑作为仪式与保温的手段陈述了折衷艺术,在形式约束的同时用功能之于生活的氛围与舒适的考量把建筑同景观一样灵活体现,其兴趣于大也关注于小、于生活之所需,感知与触摸是其动作,而精巧多样的细致帮建筑面向大众,展现了丰富和不变,不再是孤立而处(图7)。
图5:日本东京圣玛利亚主教座堂,丹下健三
图6: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院大楼,詹姆斯·斯特林
图7:德国门兴阿布泰贝格博物馆,汉斯·霍莱因
图8:美国纽黑文哥伦布骑士会大厦,凯文·洛奇
而洛奇则介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时而严肃时而华丽,时而古典时而现代,他在描绘房子的同时也把自然带进建筑,于内、于上在中庭、角落与平台盘旋,进而赋予其艺术的可能,并与纪念合鸣、与时尚缠绵(图8)。而以不规则、不明确的断裂形式来打破传统的盖里则介于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其把建筑打量成如雕塑般的艺术,呈现了独特、纷乱、抽离与神秘的气息,与现代形成巨大差距,这一切与现实无关只是灵感的传递,并解决复杂问题(图9)。
另外,不追随潮流或者符合地方文化或者参杂其他,或者从思潮的铺垫中突围以自创的是巴拉甘、玻姆和尼迈耶。巴拉甘用超现实、抽象的诗意把建筑赋予了地方文化与极简美学的营造,在现代形式的单纯与简洁之中驾驭了建筑与景观,挥洒了情感与色彩的浓厚,并让寂静、平和以及与之着迷的氛围游溢着空间,让人惊异与静默(图10)。而兼具专业与艺术的玻姆是德国表现的野性余温,在其如雕塑般的形态背后是对环境、材料、构造与色彩之于建筑考量的支撑,并以填充城市孕育出性格的离世与独立,更让建筑如宗教信仰般存在,而不存在复制,呼唤着遥远人们的投视(图11)。而尼迈耶厌倦于现代的条框与规矩,向无拘无束的曲线与意外倾诉着吸引,他认为这是解放也是新颖,是性感也是潜能,得以飞翔,并以此探究着环境、形式与结构之于建筑的逻辑,其追求的是为美(图12)。
图9:德国魏尔维特拉设计博物馆,弗兰克·盖里
图10;墨西哥墨西哥城卫星塔,路易斯·巴拉甘
图11:德国科隆伊格莱西亚青年中心图书馆,戈特弗里德·玻姆
图12:巴西巴西利亚主教座堂,奥斯卡·尼迈耶
三 反映时代,思潮诠释,主流的含义,对比后的扩充
因此由上可以看出,普奖的授予反映了时代与回应其问题以及用奖的一切(评判/人/作品/宣传/讲座)再度诠释了当下/过往盛行的建筑思潮,其中不乏信仰者和拥护者,同时也展现了普奖作为专业的建筑奖,其姿态是入世的与具有传播意义的,是属于时代的产物,亦符合大众文化;而普奖一个阶段的多届得主及其实践,呈现的是建筑学发展的(某个阶段的)主流价值,并作为建筑史历程的(总体或个人的阶段性)总结评判,既回顾过往也展望未来,提出具体的参照,建立恒常的期望,比如:1979年获奖的约翰逊在1988年策划了解构主义建筑展,其中参展建筑师之一盖里就是隔年(1989年)普奖的获得者(参展建筑师库哈斯和哈迪德之后也获普奖);而盖里的搭火车式获奖,也让普奖在这个阶段(1979年-1989年)、在思潮层面的诠释趋近于当时的完整。
但是由于获奖的区域/国家之于人数对比的差异,导致普奖及其评判范畴大部分仍停留在美国,也因此有了局限,而为了更具国际视野、更具权威性,以及在既有深度对高度与广度的扩充,普奖需要进行跨越,向世界范围内的区域探寻其他,来为其取到态度上的包容与内容上的升级。
四 以欧洲居多、亚洲其次、再来美洲(1990年-1999年)
于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1990年-1999年),普奖得主有了巨大的变化,体现在人数上,以欧洲居多,7位,分别是南欧的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1990年获奖,意大利)、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1992年获奖,葡萄牙)、拉斐尔·莫内欧(Rafael Moneo,1996年获奖,西班牙)和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1998年获奖,意大利),西欧的克里斯蒂安·德·波特赞姆巴克(Christiande Portzamparc,1994年获奖,法国)和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1999年获奖,英国),北欧的斯维勒·费恩(Sverre Fehn,1997年获奖,挪威);而亚洲其次,2位,东亚的槙文彦(Fumihiko Maki,1993年获奖,日本)和安藤忠雄(Tadao Ando,1995年获奖,日本);再来美洲,1位,北美洲的罗伯特·文丘里(RobertVenturi,1991年获奖,美国)。
五 评判维度的拓宽,中心的移转,走向国际
由上可知,普奖在这个阶段(1990年-1999年)授予的多数从上个阶段(1979年-1989年)的美洲转移到了欧洲,同时也容纳了南欧与北欧(上个阶段无南欧、北欧与东欧)、且南欧多于西欧与北欧、但尚无东欧的建筑师获奖;而就国家区分,意大利2位,日本2位,葡萄牙、法国、西班牙、挪威、英国各1位,美国则从上个阶段(1979年-1989年)的6位递减到这个阶段(1990年-1999年)的1位,而这1位还是以理论重(强)于实践并打破现代统治地位的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同样也以研究与论述(《城市建筑》)闻名并建立普遍而永恒形式的罗西和以评论家自称并涉及广泛的莫内欧都在这个阶段(1990年-1999年)获奖,代表着普奖评判的维度正在拓宽,理论之于实践,评论之于作品,角色及其功能相称互托都可进入门槛,但评判却更加的严谨,预埋了未来的伏笔;而1989年获奖的盖里也在1993年加入评委阵容。
然而,普奖得主的欧洲居多与美国递减是普奖在这个阶段(1990年-1999年)有别以往的巨大的变化,也为普奖带来区域的扩展,并直接反映了当时世界建筑潮流以(从美国转移到)欧洲为中心的实践现象,且是基于欧洲整体环境繁荣与优渥的支撑;而洲际之间的跨越让普奖走向了国际,也如同在回应时代的进行着全球化,更进行着知识的储备,带来视野的开阔与辐射角度的全面指向,即使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社会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垮台而让意识形态对抗不再是国际主流,以上仍是在欧美资本的文化体制里进行的,背景不变。
六 平行参照,区域扩展与内容升级,非一体的多元而相对
也即使跨越了,普奖仍维持原来的授予基调,并体现在普奖得主身上,而中心的移转也未阻碍思潮的翻腾,只是随着时代演进、经济形势、地方呼唤与工具革新乃至观念思辨而有了些许变动,普奖得主与建筑思潮有着平行的参照,其解释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并为时代写下里程碑式的意义。
首先,在这个阶段(1990年-1999年)普奖对甚嚣一时、从诸历史中兼容并蓄、强调文脉以及具有戏谑、嘲讽、折衷与双重特性的后现代主义给予阶段性的论定,如:独钟于复杂与矛盾的文丘里,拥抱传统,用历史与通俗来赋予建筑的审美和欢愉,并基于文本分析的把理论赋予实践的观念创新,为后现代奠定论述的基石而有其价值,这些都获得其伴侣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的支持与投入(图13)。接着,通过对类型学之于建筑/城市思考与原形论的认识,普奖关注了新理性主义,并以此开启了新的阶段,如:罗西就是代表,其实践以追寻历史的类型为其本质的追求,并赋予形式的抽象以唤醒人们的记忆,让永恒与文化浸染共时存在,建筑相似又不相似,同时从历史、地理与人类的生存来阅读城市,并以此来解释建筑(图14)。然后,上个阶段(1979年-1989年)集体亮相(1988年的解构主义建筑展)的解构主义,其破碎与扰乱的实践仍持续着,也被普奖探讨着,同时计算机的革新辅助让纸上想象与复杂形式得以落地,如:波特赞姆巴克的实践以空间的消减来处理体量的构成,以虚就实地创造出复杂形式的丰富与单一,同时用开放性原则来塑造广场、街道与内外空间在城市中的结合(图15),探索其韵律。
而始于晚期现代主义、以技术至上的高技(材料/结构/设备/科技)也随之登场,被普奖讨论着,并提出对环境与生态的重视,如:皮亚诺的实践先明确处理建筑的一切关系,对材料与结构予以细部的关注,并研讨着形式的繁复逻辑以焕发出建筑冷静的层次与递进,更与环境、与自然对话,对生态技术予以研发,让智慧、人性与诗意充溢着建筑(图16);而福斯特也对技术保有热情,同时也对生态技术与地球资源的耗尽持续关注,而其技术也回应以轻盈优雅而大气的形态,并忠诚地展现与建筑的结构组织和清晰的定位,还有能拓展的边界,而科技自觉与高度审美则是他在终点的诠释(图17)。
再来,经典历史的怀旧也插队入列,追忆的是在建筑之内对精神层面的崇高景仰,而不是后现代的历史隐喻,如:莫内欧的实践让历史成为载体,创造出具有时间意识的建筑,或者探讨着城市环境与建造现实,最终展现恒久的纪念,并有着高度的质量(图18)。
而也属于过往经典的现代主义在式微了许久,在这个阶段(1990年-1999年)有了现实的回归,并从社会、城市与材料方面导引出新的阐释而被普奖透视着,如:出身于新陈代谢运动的槙文彦,在现代的根本上,以敏感的认知对文化的凝聚、城市的理解、环境的协调以及开放结构的研究,进而衍生出顺应时代变迁的空间语法,创造建筑多层次的内涵,既融合了东西也传达了情感(图19)。而上个阶段(1979年-1989年)的主力——晚期现代主义到这个阶段(1990年-1999年)落寞了,却没被普奖遗忘,仍缓步地锁定在世界上某个区域而前进,自成话语,不去干扰其他,如:西扎的实践,在几何的现代形式中探讨着场地之于地方的场所精神的建立,把平庸提高,并让和谐与平衡在静谧处驻生,同时根据经济、历史与环境条件来组织光与材料的构成,以此向世人表明其内在生成的自明(图20)。
图19:日本东京复合文化设施,槙文彦
图20:葡萄牙波尔图大学建筑学院,阿尔瓦罗·西扎
另外,基于特定的自然特征、文化精神的构建以及采用适宜经济的技术的批判性地域主义成为了普奖新的提出(北欧、日本),如:安藤忠雄的实践以几何的现代形式、朴素材料的洗练与光影的戏剧生成,创造性地阐述了建筑与环境、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经由自然的布道与建筑的故事,仪式般地包被出无法言明的空无与虚幻,萌生自律和内省的意识,进而批判外界的复杂,成为某种地域表达(图21)。而受存在主义影响以及用一生去远离北欧传统但最终意识到不可背离的费恩,其实践也用对环境、场地、功能、材料与结构之于建筑的感知、直觉般的把握去解答自己的存在和地域的缪思,同时寻求历史与现在的平等,更以不打扰自然的对自然的执迷追寻其永恒(图22)。
图21:日本大阪茨木春日丘教会,安藤忠雄
图22:挪威冰川博物馆,斯维勒·费恩
因此由上可以看出,普奖在这个阶段(1990年-1999年)以区域的扩展揭示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实践现象,在走向国际的同时也积极迎来了内容的升级,有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付诸,有思潮于阶段中的滚动痕迹及其延伸,更和普奖得主形成平行的参照,既有回顾亦有展望更立足于当下,非一体的多元而相对,坚守又推进;而普奖也因此展现了国际的视野,影响力与日俱增,另外亚洲建筑师的无缺席,让微弱又有力的东方声音被听见,点睛力度鲜明,但尚未有大洋洲与非洲的建筑师获奖。
七 仍以欧洲居多、美洲其次、再来大洋洲
(2000年-2009年)
再来,到了新世纪的21世纪初(2000年-2009年),普奖得主仍以欧洲居多,8位,分别是西欧的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2004年获奖,生于伊拉克,英国)、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2007年获奖,生于意大利,英国)和让·努维尔(Jean Nouvel,2008年获奖,法国),北欧的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2000年获奖,荷兰)和约恩·伍重(Jørn Utzon,2003年获奖,丹麦),中欧的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2001年获奖,瑞士)和皮埃尔·德梅隆(Pierrede Meuron,2001年获奖,瑞士)与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2009年获奖,瑞士);而美洲其次,2位,北美洲的汤姆·梅恩(Thom Mayne,2005年获奖,美国)和南美洲的保罗·门德斯·达·洛查(Paulo Mendes da Rocha,2006年获奖,巴西);最后是大洋洲,1位,格伦·马库特(GlennMurcutt,2002年获奖,澳大利亚)。
八 超越了性别,密切协作的提出,扩展再扩展
而就国家区分,瑞士2位,英国2位,荷兰、丹麦、法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各1位。可以观察到,作为20世纪下半叶的强权、有着众多建筑师的驰骋、且是普奖策源地的美国在20年内(1990年-2009年)只有2位获奖者(文丘里,梅恩),此情况甚为特殊,尤其是在晚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后才发生的诡异?或许是美国在普奖头10年(1979年-1989年)获奖者居多(6位)而造成之后20年内给人概率(假性)不平衡的冲击,但若就每个阶段的国家比例而论,实际上是平衡的;而普奖在这个阶段(2000年-2009年)首次授予了女性建筑师,哈迪德,也首次授予了一对组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合伙性质),说明着一件事,即超越了性别与密切协作的提出都让普奖再次的进取,更扩大了群众基础,而区域的再度扩展体现在马库特是大洋洲的首次获奖,而亚洲在这个阶段(2000年-2009年)则无,非洲依然未有建筑师获奖。
另外,1989年获奖的盖里在2002年再次加入评委阵容,1998年获奖的皮亚诺在2007年加入评委阵容,而2004年加入评委阵容的多西于2018年获奖,2006年加入评委阵容的坂茂于2014年获奖,2008年加入评委阵容的阿拉维纳于2016年获奖,因此可以看出,之前获奖的加入评委阵容(盖里、皮亚诺)与加入评委阵容后、任期届满卸任而在未来获奖的(坂茂、阿拉维纳、多西),以在这个阶段(2000年-2009年)出现的最多,是蛮奇特的现象,或者只是巧合,而普奖也扩大了提名权(自2009年起征求往年得奖者、学者、评论家与其他在建筑领域具专业知识与兴趣人士的提名),纳才不言可喻。
九 主义的漠视,聚焦于议题,广泛深刻而又细致
而世界建筑潮流以欧洲为中心的局面,在这个阶段(2000年-2009年)方兴未艾,但不代表其他区域没有动静,而上个阶段(1990年-1999年)的思潮也演进到这个阶段(2000年-2009年),因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扩张(把世界视为一整体),让思潮之于世界的发展、区域的性质发生了质变,不再是唯一,并发对(大)主义论的漠视,解构以降最为明显,由此衍生了对既有的反思,或者走向歧途的批判;与此同时,在满足人类需求、珍惜资源与环境平衡以及在过往至今的内容上,在这个阶段(2000年-2009年)普奖有了对建筑学投以多面向的关注,在保有专业(设计)的同时,从主义的宣示转向了对议题的挖掘(如:城市、网络、生态和数字化等),并以此来对话与批判传统;而议题的挖掘也形塑出对议题的聚焦,让思考投射于微观,却以宏观的视角放眼全球来应对,不局限于某个区域,赋予解释的开放性;所以,建筑师朝向以世界建筑师自居,而非以主义建筑师而前进,但却摆荡在建筑学核心与边缘之间进行探索,其成果也无视与避免于形式的归咎,觉醒地让位给局势或是建筑的其他。
因此,在这个阶段(2000年-2009年)普奖授予的基调再度扩增,悄探议题,真实地反映在普奖得主的实践上。首先,针对城市,库哈斯认为建筑(从社会学入手)需面对城市新问题(网络与社会、新时代的生活、城市发展速度、资本等)并予以先进的解答,其用颠覆与跳跃的论述冲击着传统,也冲击普奖的评判,建筑必须从永恒中解放是为急迫,但他却保有实践的恣意(图23);努维尔也关注城市,认为建筑的生成是构建在周围城市的(多层次)信息及其内涵与人们对此的认识,外部的联系强于内部的考量,并用材料与光的丰富性来表达建筑的透明与复杂,感性又诗意,他也认为建筑是对转变、揭露、延长与分析的思辨(图24)。生态是马库特提出的,普奖对生态并不陌生,在上个阶段(1990年-1999年)就有生态技术的高技探讨,而马库特的生态是低技的,正好与高技形成对比,其轻轻触摸大地的形式是对环境敏锐的感知,举凡地形、海拔、风力与日照等因素之于设计的评估后,其方式是解决而非预设,以及扛起对环保的责任(图25)。
而计算机在上个阶段(1990年-1999年)以后的飞跃奠定了数字化建造及其范式的形成,给予了建筑无限与未知的机遇,并透露着解构的成熟与批判传统的始终,如:在数字化范畴中,构建人工地景与地形学的哈迪德,其空间组织与结构所产生的流动形式,无缝的充盈而饱满并富有想象,激发了社会的活力,也霸气而优雅地对抗常规,批判着传统(图26);而梅恩以模弗西斯(Morphosis)的创新逻辑,让建造的理解进入到图绘的现实,并再思考地转换为破碎的生成,无人能预知其结果,但却展现了拼凑、撕裂与群组的构件和形态,对现实、对传统是既顽强抵抗又莫名的协调(图27)。
而在数字化其形式奔放的同时也有着拘谨的纯粹形式的现代回归,并与材料进行新的捆绑而推演出新的构建(体系、氛围),而现代回归普奖很熟悉,但与材料捆绑,诱发了普奖投以新的关注,如:强调本体论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以纯粹形式对(多种)材料之于建筑予以精确的建构,从锁定表皮与节点到总体结构的把控,钜细靡遗,这是继承了(瑞士)新现代而衍生的新方向,之后成为时尚,也让他们警惕(图28);而卒姆托也以纯粹形式的定制理念,让材料/构造之于建筑本质的思考,折射出某种哲学的默示,进而使空间成为了生活的日常,体验与感受其氛围成为了必须的真实,以此来对话传统,并孕育其如诗般永恒的存在(图29)。而洛查也忠实而明晰地运用材料的特性及其未加工印象,把建筑推向极致而又裸露的结构表现,以此营造出野性而素朴的现代形式,从而包裹着诗意的空间(图30);而扩大材料意义而让技术与结构占据主导的罗杰斯,实际上是高技的延续,他让建筑成为大尺度的框架,把生活的一切填充入内并予以重叠,容纳了人性与进步,并向外界述说着当代的片断,既灵活又耐人寻味,之后更关注气候变化与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影响(图31)。
而伍重的实践扎根于更为广泛的文化,有他者的,如:玛雅、中国、日本与伊斯兰文化,以及属他自己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从而创造出极具感性与热忱的形式,于中谈论着与天、与地、与人和与自然的关系,是现象学之于建筑的缪思,更与上个阶段(1990年-1999年)的存在主义有所呼应,吸引着普奖(图32)。
▲图28-32(向左滑动查看)
因此由上可以看出,仍以欧洲为中心、区域再扩展、超越了性别与密切协作的提出是普奖在这个阶段(2000年-2009年)的授予现象,更因新世纪之后人类发展之于全球环境、世界局势的演变而使普奖得主对多面向的议题投以关注与应对,致使其众声的实践所缔造出来的集体内容让普奖再次得到了升级,步伐更为开阔,在少谈主义之时因而研究不少,而普奖与其得主也更加立足于当下去思考未来,对于过往只是点水般的敬仰,如此,多元已是常态,议题的聚焦和各自的解释,广泛深刻而又细致,引领着建筑学的发展。
十 以亚洲居多、欧洲其次、再来美洲(2010年-2020年)
到了21世纪10年代(2010年-2019年)以及今年(2020年),普奖得主又有了和以往不同的巨大变化,体现在人数上,以亚洲与欧洲居多,分别是7位:在亚洲部分,有东亚的妹岛和世(Kazuyo Sejima,2010年获奖,日本)和西泽立卫(Ryue Nishizawa,2010年获奖,日本)、王澍(Wang Shu,2012年获奖,中国)、伊东豊雄(ToyoIto,2013年获奖,日本)、坂茂(Shigeru Ban,2014年获奖,日本)和矶崎新(Arata Isozaki,2019年获奖,日本),南亚的巴克里希纳·多西(Balkrishna Doshi,2018年获奖,印度);在欧洲部分,有南欧的艾德瓦尔多·索托·德·莫拉(Eduardo Souto de Moura,2011年获奖,葡萄牙)和拉斐尔·阿兰达(Rafael Aranda,2017年获奖,西班牙)、卡莫·皮格姆(Carme Pigem,2017年获奖,西班牙)和拉蒙·比拉尔塔(Ramon Vilalta,2017年获奖,西班牙),中欧的弗雷·奥托(Frei Otto,2015年获奖,德国),西欧的伊冯·法雷尔(Yvonne Farrell,2020年获奖,爱尔兰)和谢莉·麦克纳马拉(ShelleyMcNamara,2020年获奖,爱尔兰)。而美洲其次,1位,南美洲的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2016年获奖,智利)。
十一 东移的文明复兴,全球视野,授予中国与印度的首次
由上可知,普奖在这个阶段(2010年-2020年)授予的多数,亚洲与欧洲是相同,那是因为有了两对组合与一个团体(3人以上包括3人)的获奖,亚洲的是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日本),而阿兰达、皮格姆和比拉尔塔(西班牙)以及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爱尔兰)就属欧洲;而若就每一年普奖得主及其国家来区分,2010、2013、2014、2019年由日本,以及2012年由中国与2018年由印度分别获得,共6年由亚洲获得,而欧洲获得的4年,2011年是葡萄牙、2015年是德国、2017年是西班牙与2020年是爱尔兰,由此可见亚洲获得的比欧洲多,也就是说普奖在这个阶段(2010年-2020年)授予的多数从前两个阶段(1990年-1999年,2000年-2009年)的欧洲转移到了亚洲,而若从1979年创立那年算起至今,普奖授予的多数共有两次横跨,先从美国到了欧洲(1990年),再从欧洲到了亚洲(2010年)。因此,普奖再度进行区域的扩展、洲际之间的横跨,就地理而言幅度更大,来到了以亚洲居多的时期,有别于以往的点睛;而如此聚焦亚洲,除了获奖建筑师的优秀,其背后是亚洲文明复兴的支撑,并架构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纵横捭阖中的全球权力的东移,获奖建筑师所属的国家在当代发展中皆取到了成功,日本以及韩国、越南与新加坡的稳定,中国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崛起,印度的经济腾飞,都让世界为此注目,进而想了解其文化,普奖也是,而宽广浩瀚的全球视野也为普奖迎来了权威的肃立。
而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打破了日本建筑师从1995年以后有15年未能获奖的过程,此后,日本建筑师更持续地获奖,有伊东豊雄、坂茂和矶崎新,获奖频率之高,相似于1979年至1989年(普奖设立的)早期阶段的美国建筑师获奖居多的情形,其中坂茂和矶崎新皆是评委卸任后才获奖的,西泽立卫则是最年轻的得主(获奖时年仅44岁);之前,亚洲的获奖以普奖授予日本建筑师为主,而在这个阶段(2010年-2020年)则有了亚洲其他国家的获奖,如:普奖首次授予了中国建筑师王澍,而卸任评委的多西也获奖,他是印度建筑师,而较早(2011年)也首次有中国建筑师张永和加入评委阵容;另外,2002年获奖的马库特和2004年获奖的哈迪德于2011年加入评委阵容,2007年获奖的罗杰斯于2014年加入评委阵容,而2010年获奖的妹岛和世和2012年获奖的王澍于2017年加入评委阵容,由此可见,获奖后加入评委是普奖评委增补的惯性之一,而卸任评委的阿拉维纳也于2016年获奖。
十二 趋同与逐异,人类社会的赋予,地负海涵的绵延
建筑之于亚洲文明的复兴与普奖的亚洲建筑师获奖的增多其背后隐含了一些关于体制与文化的成因和趋势。因世界经济发展推动着全球权力的东移,导致中国的社会或者亚洲其他的文化体制也能同欧美的资本一样参与到机制中、被建筑讨论着,削弱了建筑潮流在过往以某个区域(欧洲、美国)为中心的实践现象,并使其均等化地覆盖,不再只是欧美;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当国际政治不再跋扈对抗,转变成经贸依存的自由竞争,也刺激了区域内的文化逐异的多元形成(亚洲便是如此),也就是说,趋同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逐异是共存的,展现了一种时代宽容的气息;所以循此思路,普奖在这个阶段(2010年-2020年)有意识地在文化上着力而形成其价值的参照,在建筑艺术上保有既有的趋同也鼓励文化逐异的讨论,让审视的维度更为宽广,并以全球/世界/区域作为大环境背景的之于建筑的考量与评判,进行再度升级也予以丰厚的凝聚,而主义论也不再只是建筑从漠视走向开放的于人类社会的赋予。
因此,在既有的建筑学以及上个阶段(2000年-2009年)的议题(城市、网络、生态和数字化)延伸探讨时,在这个阶段(2010年-2020年)又产生了关于地球资源、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生活住居的新问题,让获奖建筑师在追求建筑艺术之时也谨慎面对这些问题给建筑的影响并给予适切的回应,其中有的获奖建筑师所面对的议题是恒久的、起始于上个世纪,所以,总的来说在这个阶段(2010年-2020年),普奖有了对地球、资源、自然、气候、环境、地貌、社会、经济、地方与国际、过去与现在等议题的探讨,议题之于议题也于一位获奖建筑师的实践中辩证着,并依不同区域、视角有着差异的创造性解决,探究得更为深切长远,而让普奖授予的基调的再次扩充,真实地反映在普奖得主的实践上。
首先,社会与经济的议题是多西和阿拉维纳探讨的。多西通过整合建筑设计出层叠交融的低造价住宅,为中低收入者创造了居住环境(图33),而阿拉维纳则以关注全球住房危机投入到低成本的社会保障房的建设,两人皆以此回应了经济的现实,并积极与居民、政府、建筑商与施工队紧密协作,争取各自的利益,因此,建筑师的功能定义被多西和阿拉维纳两人扩大了,成为社会参与的统合者和协调者,而阿拉维纳还针对保障房,主动释放建筑师权力,提出半成品的房子,让使用者来完善以增加其投资兴趣(图34)。另外,多西和阿拉维纳也关注了自然与气候议题。多西以气候的考虑协调出空间的多样转化(捕风捉影)并附以材料丰富(预制件、工艺)的应用,加上对印度传统的理解,让建筑兼具功能与体验,且地方性浓厚,富有哲学与诗意,并贯彻了可持续性,达到和谐、包容与谦逊的境界,而阿拉维纳则把隔热与通风、降低能源消耗体现在双层墙与中空中庭的设计,在其简洁而有力量的现代形式背后,诚实地面对了区域内的自然特征,予以解决。
图33:印度印多尔阿冉亚低造价住宅,巴克里希纳·多西
图34:智利社会保障住房,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
阿拉维纳更关注自然灾害议题(地震、海啸),参与救援与重建,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提出了在岸边植林以减缓灾害的冲击,而坂茂和伊东豊雄也对此议题投以关注。
在面对自然灾害(地震)抑或人为灾害(内战)时,与阿拉维纳一样有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坂茂,提出以建筑的方式解决灾难民的流离失所,并创立(非政府)志愿者组织投入到全球的救灾以及善意的在场坚守中,还在考量灾后复原时,提出以低成本、便于拆卸、可重复使用的材料与结构体系的建构,以适应重建乃至特定环境与场域的建筑解决,让人们得以庇护(图35),而伊东豊雄也投入到自然灾害(地震,海啸)的复原,重新亲近大自然,为灾民设计共有之家,用材料做出最低限度的建设,并以探讨建筑的初源来质问建筑本质的意义,两人共同延伸了建筑的内涵,渗入了活力与人性的关怀与尊重,柔化了建筑刚硬的外表,赋予其情感。另外,关于创新,坂茂和伊东豊雄就有了不同的诠释,坂茂的创新体现在材料的复合与应用,并引申出不浪费、可持续性与环保的理念,而伊东豊雄的创新则体现在一路走来的建筑追求,不重复既往,在设计中把结构、空间、技术与场所周边条件融为一体的考量与建造,探索如自然般的复杂、多变与流动的形式,以突破常规的挑战现代的功能与效率,让人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图36)。
图35:新西兰基督城纸教堂, 坂茂
图36:日本东京多摩美术大学图书馆,伊东豊雄
接着,王澍、莫拉和奥托则以材料的视角探讨了资源与经济的议题。材料的回收是王澍关注的,并提出了材料的经济适用,以此回应了资源审慎的见解(图37),而莫拉则以不使用濒临灭绝的材料,以及使用木材后需种植新树木的对自然的回馈,以此述说了资源珍视的观点,而奥托则从大自然中激生灵感、通过理解事物形成的研究过程,把(多种)材料以最经济的方式创造出轻巧又精巧的轻型结构,且兼具功能、美观、适应力强与易拆解,并引出了审慎利用资源、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观念(图38)。三人的材料有重(砖、石)有轻(木、帐篷、网壳、竹),但同时指向了审慎与珍视,材料不同,立场却相同。
图37:中国浙江宁波博物馆, 王澍
图37:中国浙江宁波博物馆, 王澍
而王澍也以材料的回收关注了久远的过去,在探询往昔之时,唤醒了历史在今时的新生,随着时间的流转,追问着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中国城市化的反思),这些都架构在其认为建筑是业余并让位给生活的思路上,坚守着在特定文化与区域的归属和实践。而环境与自然之于建筑的关系也是莫拉关注的,在其看似简单的现代形式中,潜藏了对场地周边的协调与融合(景观、地理与历史),并突出人为与自然的对应,还用材料与色彩给予建筑非凡的定义,并认为这一切是建造(图39)。而奥托的实践更多是与工程师、生物学家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协作的集体成果。
再来,自然与地貌的议题是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与阿兰达、皮格姆和比拉尔塔探讨的。具有人文意识的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以对地球负责为己任,关注了自然资源与气候变化,在其创造的空白缝隙中,引入光线带进微风,改善物理环境的损耗,增加了可持续性,并以取之地球的回馈,希望用建筑、地形帮助地球永保它的美丽(图40),而阿兰达、皮格姆和比拉尔塔则关注了不同场地的历史、自然、物理与文化特征以及予以认识后,以因地制宜的关联设计,让环境、地貌、景观与建筑达到协调与融合(图41)。而两组人也对材料各有不同的运用,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以对材料的研究进而发展成一项匠艺,给予建筑表皮新的开拓视野,而阿兰达、皮格姆和比拉尔塔则用材料的纯粹、虚实与工艺赋予建筑一切(内与外、新与旧、现在和未来)的联系。
而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与阿兰达、皮格姆和比拉尔塔也探讨着城市与环境的议题。法雷尔和麦克纳马拉以介入城市的思考,对场地的城市周边与环境场域投以关注,同时把建筑创造出具有社交回旋的社区意识,进而形成底层向城市开放的回馈,让建筑成为城市中的公民而有所贡献。而阿兰达、皮格姆和比拉尔塔则注重了建筑的超越既定、不受时间的限制与意想不到的结果,以及连接过去与现在,以此来服务社会与社区,唤醒人的情感。社区,就成了两组人的共有词,有其差异,一组是社区在建筑之内的开放,一组是社区在建筑之外的联系,而两组人也同时展现了根植地方、前进国际的实践状态,在建筑中追求两者的并存。
而环境与自然也是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所关注的议题,她们创造了同环境相容、扣合与互动的建筑,轻盈又流畅,并赋予其开放的美好,也把空间推往平静与深远,展现暧昧又迷离的极致,更丰富了体验的饱满(图42)。矶崎新也关注城市议题,探讨着建筑在城市之中的问题(过去与未来),且是基于对历史、文化、哲学与理论的深刻理解后所提出的论述,而他也力求创新,架构在长期游走于东西之间的不断探索与尝试,既不安于现状,也勤于融汇,更勇于唤醒与挑战当下,其实践统一于全球和地方(图43)。
因此由上可以看出,亚洲文明复兴、区域再扩展、全球的视野,授予中国与印度的首次以及文化解释的创造是普奖在这个阶段(2010年-2020年)的授予现象,获奖建筑师在保有专业的同时,亦展现对议题层面较过往更加广泛的深入,浓密而长远的交缠着,把建筑安分于当下亦推往未来的等待,而独到与深刻也体现在建筑师角色的针对,进而扩大,有关乎社会参与的责任、关乎心理层面的建设、关乎人道的立场与应对、关乎地球与自然的守护、关乎道德伦理的述说,这些都让普奖绵延得地负海涵般,持续引领着建筑学的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四十四年的普奖,从1979年至今,每一年的评判与授予乃至每个阶段的递进其背后皆有想要传递的信息,以及所引申的关于建筑学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及其方向的明示与窥探,在经过每个阶段横跨的幅度与世界局势的演化所产生在中心与边缘之于话语的蜕变,以及蜕变后内容的叠加、升级与扩充所形成的丰厚凝聚,就如同是在谱写一部前进的世界建筑史,华丽的篇章不曾间断,镶嵌过去、面对当下以及迎向未来;当然,除了普利兹克建筑奖,世界上还有其他重要的奖项,如: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金奖、阿卡汗建筑奖、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金狮终身成就奖、密斯·凡德罗欧洲当代建筑奖、中国梁思成建筑奖、美国建筑师学会金奖、世界建筑节最佳建筑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等等,部分普奖得主也在以上奖项留下了痕迹,而成就一个奖项的权威,其要义是获奖者的优秀强大和绝对贡献以及评判的慧眼睿智,缺一不可,铸就辉煌就成为了共同的追求。
而从前文得知,群星灿烂的四十二年的普奖得主皆来自北美洲、南美洲、西欧、中欧、东亚、南欧、北欧、大洋洲与南亚的建筑师,当然也知道普奖是在欧美资本主义的文化体制里成形的,相对有其语境上的判断,而中国建筑师王澍于2012年的获奖是普奖授予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首次,指标、象征意义浓重,但是除了中国,(瓦解前后)社会主义还包括前苏联与前东欧集团,如: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在它们处于冷战时期(1950年以后)乃至瓦解前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建筑展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话语,自成体系,倾向于苏联先锋、构成以及意大利未来、德国表现、晚期现代余韵的社会主义现代主义(Socialist Modernism)的实践,对比于(欧美)资本主义现代主义(CapitalistModernism)则更为的丰富与奔放,有其背景、现实因素、信仰和不可替代性。
因此,值得普奖以及建筑学人予以关注,冀望在未来,有它们的建筑师获奖来让普奖海纳与完善,更完整的谱写世界建筑史,而对于下一届普奖的想象,已是当代的显学,存在就是现实,那就让我们来拭目以待吧。
作者:黄元炤/Huang Yuanzhao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现执教于ADA研究中心;在现代历史意识语境下,长期从事建筑(史论)之于时代的构建与整合、拓展与凝聚的研究工作,以及观念、思想和价值取向的文艺批评;在多家杂志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并出版多本学术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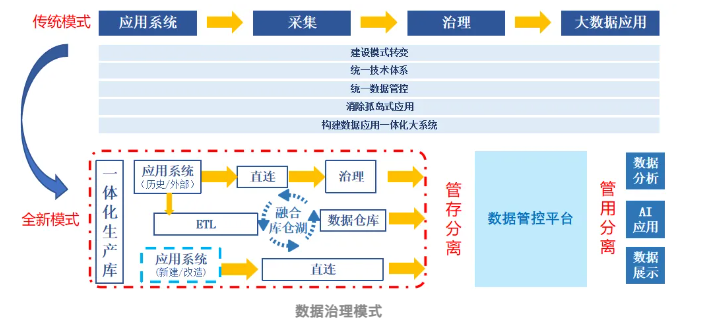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